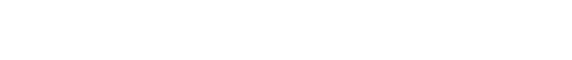
■黄石市城市水务集团 吴炜琪
这世间不是所有的事物从一出生就能落入他们该有的环境,适宜的土壤、优质的空气、充足的阳光、丰盈的雨露,一如有些树,它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如自由落体般滑入了湖边、河滩、水中央,水深火热、泥沙俱沉,年深日久小小的种子开始发芽,百转千回中长出小小的小树苗,只是同树不同景,在岸上、水边迥然不同的空间里成为生命的另一种形态。
那天我和姐姐为了能观赏一场湖边晨雾的景色,披着朦胧的月影驱车穿过一片枫树林,来到名为奇墅湖的湖边等待一场云雾蒸腾,然而天空之色、云雾之起落岂是时时能随心所愿的。等待许久、张望了许久,晨雾未起,烟云漫漫,我们心有不甘的与一场晨雾失之交臂,对于天象而言唯有等待方能见奇迹,那些和我们一样早起的摄影爱好者们架着镜头,依旧痴心不改的在偌大的湖面河滩捕捉着晨雾之外的风景,山峦、秋色、水鸟,还有……蓦然回头,我看见了几棵长在湖中央的树,水退石滩露,在冷冷的寒风中、在薄明的晨曦里,它们身形单薄而瘦弱,每一根枝干都向上伸展,苍劲有力,细细数来,荒凉的湖滩不过三棵树,风在纵横,狠狠越来湖面拍在湖滩上,我们的衣角、发丝在风中零乱,我想要撤回到车里,姐姐说好不容易来一趟赏赏这与众不同的风景,于是我们开始在湖边徜徉,不远处是那三棵树在风中挺立,我时而望向湖面与山峦,时而开始细细的端详起这三棵树,它们伫立在风中的形态各不相同,但每棵树都能自成一景,它们的根扎在湖水退去后稀松的沙土里,小小的树枝上叶片寥廖,诠释着凋零的落寞与孤寂,躯干如被炭火烤过一样泛着黑色的光,像一个生命浴火重生的样子。此时的湖面正值枯水期,平静如镜,我此时站立的河床是湖水退去后裸露出来的空沙地,也就在这短暂的季节交替中,这些曾被淹没在水中的树获得了重见天日、重获新生的机会。
望着这些似曾相识的水中树,不禁让我想起了家门口的那片湖磁湖,围着磁湖有一圈杨柳,杭州西路四季美如画,有一半的风采来自于沿岸的杨柳青青柳色青,看的见的永远是风景,看不见的拐角也有遗落的生命在求生,几株水中柳,它们以濒死之态横卧、倾斜于湖面,横卧者卧而不倒,倾斜者则牢牢吸附于岸边,一眼望去可谓东倒西歪,枯萎残败,像一幅揉皱的油画留置在了人烟稀少的湖面拐角处,就一棵树的站位而言它们生长的环境是恶劣的,湖水在季节里潮起潮落,终有一天它们会被再度淹没,冰冷的水面和沙土漫过树根、树干、树尖,在粼粼的柔波里被抹去的了无痕迹,好似一棵树、一个会呼吸的生命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般。然而幸运的是,我领略了它们短暂而残缺的美,在水退去的地方我捡拾到了生命的本真,它们空洞枯萎确又倔强的从水中浮出,在无人问津的僻静处自我伸展,自愈疗伤,比不了苍天大树、百年古木,无法被人珍藏和保护,也不被众生欣赏,如此的这般并不符合一棵树成长的心语,如若能语,它们渴望上岸,像那些正常生长的树一样接受阳光雨露的滋润,变得伟岸而挺拔,然而一如命与运在时光中捉摸不定的游走,难以把握一样,这些在水岸边死去活来的树,生长、淹没、腐蚀、再生长、再沉入水中,生命在渡劫中一次次向水而生,终身长不成一棵伟岸标准的树木,只能以残缺之态叩问天地,唯有在水退石出时,它们像一把伞将生命的骨架撑到极致,彰显卑微生命的极致之美。触情生情、莫名的亲切感并非一句莫虚有的说词,这些树的生命痕迹于我而言就是母亲生命的映衬,半生于疾病抗争,确从未抱怨悲戚过,日子如常,她也如常,在平静的接受与抗争中彰显着顽强与乐观,用爱与坚持笑傲生命的残缺,她细心而专一的养育了两代人,她有动人的歌声,常常自弹自唱,她与书籍为伴,一遍遍的翻阅让内心充盈平和而美好,她与人为善,充满对生命的同情与怜悯,她的精神气质让生命充满韧性与张力。
我走近这些水中树,发现在它们看似腐蚀的老树干上也分出了新枝,长出了新柳条,虽弱不经风的在尘世飘飞,也是新生;我还看见了一些人站在树的身旁定格下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之美,将一份生命的信念和不朽的画面永远记录珍藏下来,向上向阳向着希望而生。生命之树,种在心中的树。